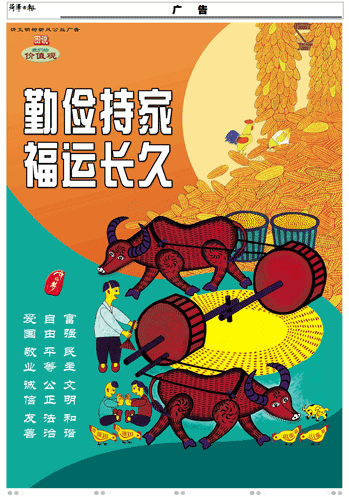人生最好的见识就是行走,走出门去,照顾那些山水霁月、历代星辰。
有人说在异乡停留一周,大致就会融入这个地方。七月大热的时令,有机会去无锡徜徉数日,品得“三味”。
烹小鲜不易
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但是有过美食经历的人都知道,没有一味小鲜是容易烹制的。
无锡小笼包是当地的一道传统名吃,已有百年历史。它选料精细,小笼蒸煮,具有夹起不破皮、翻身不漏底、一吮满口齿、味鲜不油腻等特点,若秋冬季节,在馅中加入熬熟的蟹黄油,即为著名的“蟹粉小笼”,鲜美可口,尤难忘怀。
花雕冰醉小龙虾的制作更是让人惊叹:第一步,花雕酒、葱姜蒜、八角、香叶、话梅,放在一起煮开,关火晾凉;第二步,冷却后加入白砂糖、盐、花椒、干辣椒、香糟卤,搅拌均匀,这就是卤汁;第三步,清洗干净小龙虾,加入白酒,浸润20分钟,洗净龙虾;第四步,清水加葱姜蒜、料酒,放入小龙虾煮熟;第五步,准备冷开水,最好是冰水,把煮熟的小龙虾过冷开水,之后放入卤汁中浸润,再放入冰箱,冰醉几个小时后食用,那鲜美冰爽馥郁的滋味,让人词穷。
不吃“三白”,枉到无锡。“三白”是指太湖白鱼、太湖白虾、太湖银鱼,由于色泽均呈白色,因而称为“太湖三白”。这道菜的制作工艺并不烦琐,多为清蒸白灼,保持原味,但这道菜极为注重食材的新鲜程度,因其出水极易死亡,故而最适合在水边或船上烹制,讲究的是一个天时地利。
这些小鲜们,个个工艺精湛,制作不凡,足见匠心。
问题来了,老子为什么大言不惭地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也许老子那个年代,没有炒锅,没有花生油,没有辣椒,没有香菜,给他个小鲜他能咋办,他也只能胡乱地在简易的灶具里煎几下,然后囫囵地吃,所以觉得容易。
当然这只是说笑。
一般情况下,小鲜基本上都是各地美食小吃,都是土生土长,代表一方水土。拿北方的羊肉汤来说,每个地方的羊肉汤味道都不尽相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同一种味蕾的追寻。
张翰因见秋风起,顿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而归。
美食,不仅是味蕾的记忆和满足,更是唇齿间的故乡。
守住美食,其实守住的是故乡,是家园,是精神的肚脐。
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让人们自由地生活,美美地吃饭。
大剌剌一派山水
北方多人文景观,南方多自然山水。
太湖的山水,懒得人文雕琢,就是大剌剌绽开一派自然的风光,烟波浩渺地等你来。
鼋头渚是太湖绝佳处,之所以叫鼋头渚,是因为附近如龟的充山一头扎进湖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观景带。这里曲径通幽,浓翠逼人,湖面如白玉盘,青山似螺髻,远望襟三江,吞五岳,气象万千。
来往太湖曲,三顷碧波可濯足,也不得不吟诗。诗词与美景的碰撞,美得让人沦陷,尤其是雨后初晴,满湖诗意迭来:
“渔船载酒日相随,一笛芦花深处吹。湖面风收云影散,水天交照碧琉璃。”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吹来忽不见,鼋头渚下水如天。”
鼋头渚之所以闻名,是因为有郭沫若的题诗:“何用垒山庄,蠡园太矫揉。亭台亡雅趣,彩色逐时流。无尽藏抛却,人间世所求。太湖佳绝处,毕竟在鼋头。”
蠡园地处蠡湖之滨,相传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偕美人西施曾泛舟于此,故取名蠡园。蠡园本就是人家小情侣的后花园,堆砌点石头,修建个亭台楼阁,雕琢个景观,无可厚非。蠡园的人工假山当然不能与伸向太湖远处的鼋头渚的湖光山色相比,两个景观放在诗里刻意比较,就有些曲意逢迎的味道。
太湖之美在于懒,不梳妆。太湖边上的人说话也不愿意费力气,不愿意读完字词的完整音节,读到前半部分就完事了,比如读“太湖”,“太”听起来像“它”,湖干脆读成了“u”,并且轻声化处理。
爱管闲事的江南人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小日子里安逸已久,猛地听到这副对联,让人自惭形秽,以致汗流浃背。
无锡有一处读书人该去的地方,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朝圣之地,那就是东林书院。书院始建于北宋政和元年,是著名学者杨时在无锡的讲学之所。东林书院元代废为僧区,明万历三十二年,革职里居的原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其弟顾允成与高攀龙等人共同募资在原址修复,并聚众讲学,指陈时弊,随意评点、裁量当时人物,自称“东林党人”,引起朝野震动,一时间倾慕的有,嫉妒痛恨的更是大有人在,后来得罪魏忠贤,诏毁全国书院,东林首罹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