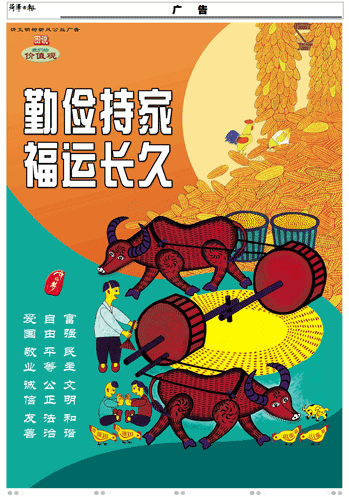“话匣子响了,都起来吧,等会吃过饭还要到地里拾柴火。哎!有一点法都不让你们下地。”太阳刚出来,母亲无奈地喊道。那时家里没有钟表,都是听挂在堂屋门上的有线广播喇叭报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哥哥在菏泽老家郭鲁生活,父亲远在百里之外的曹县工作。那时我们几个都上学,只有体弱多病的母亲一人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挣工分,秋后生产队分的秫秸、棉柴少得可怜,我家每到年关前后都会出现没柴火烧的窘况。
各自喝了一碗红薯玉米粥,姐姐和二哥各自挎个柳编篮子就出门了,我也吵吵着跟了去。正是寒冬腊月天,走到村庄外面,北风刮得更猛了,那土路都冻裂了缝。“咱到东边的吴庄去吧,那边有个桐树林子落的叶子多!”姐姐跟二哥说。
“肯定是吴庄的人来拾过了,要不咋恁干净。”跑到桐树林一看,树下的落叶寥寥无几,二哥边嘟囔边捡拾着树叶说。姐姐发现离树林子远些的地方有被风刮过去的树叶,忙跑过去拾。
我拿着母亲用筷子削的竹扦子扎着地上的桐树叶子,等竹扦上的叶子满了,我就把树叶用力往竹扦后面的细绳子上捋。不一会儿绳子上的树叶儿串成一小串了,我拉着走,那长长的树叶串儿看上去就像蠕动着的大毛毛虫。
姐姐的经验是,越是地势高的地方越没有柴火,有坑有洼的地方往往有被风刮过来积存在这里的树叶,姐姐用双手小心地捧起放在篮子里。田垄里有些刚被大风吹过后露出头来的秫秸疙瘩,姐姐和二哥赶紧跑过去拾,唯恐它被风吹跑了。
一直到除夕,我跟着姐姐和二哥每天都到地里去拾柴火。姐姐和二哥的手冻裂了一道道口子,母亲要烧热水让他们烫,姐姐不肯烫,说烧水还要费柴火。
天空中不时传来爆竹的炸响声。除夕这天,父亲和大哥从百里之外的曹县赶回家过年。父亲带来一个猪头和一些糖果、炮仗,我自然兴高采烈起来,跟着父亲的屁股后面转悠。“今晚上你到村西头请你二老虎叔来咱家吃饭!”父亲叮嘱我道。二老虎叔和父亲是发小,他中等个头,方脸黝黑,憨厚少语,和父亲最谈得来。
屋当门的案板上,放着一碗白菜粉条和一碗用猪舌头拌的凉菜。二老虎叔过来后先是往厨屋里看了看,然后和父亲打个招呼忽又转身走了。父亲正纳闷间,过一会儿从院子里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原来,二老虎叔从他家里扛了一大捆秫秸柴火回来了。
“厨屋里就那么点柴火,过年做饭咋够烧?”二老虎叔边往厨屋放柴火边说。父亲和母亲在一旁激动得不知说啥好,忙拽着他的胳臂往堂屋走。二老虎叔一边坐下一边摘下打着几层补丁的棉帽子,头上立刻升腾起一团白色的雾气:“老哥,无论多难,咱都得过年!”
忽然,姐姐在一旁突然哭了。她拉着我的手说:“三弟,初一过年这天咱不用下地拾柴火了!”也不知怎的,我跟着姐姐竟也哭起来。
后来才知,那时二老虎叔家日子过得比我家还要艰难。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小儿子,全家挤在一间土屋里,全靠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分些粮食吃,粮食不够吃就在地里挖野菜。但他豪爽仗义,就是自家再困难也要帮衬别人。
几十年的光阴如梭而过,又临春节。每当我做饭打开燃气灶,望着那欢快跳跃着的蓝色火苗儿,就回想起姐姐和哥哥冻裂的手,回想起二老虎叔送的那捆永远温暖着我的秫秸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