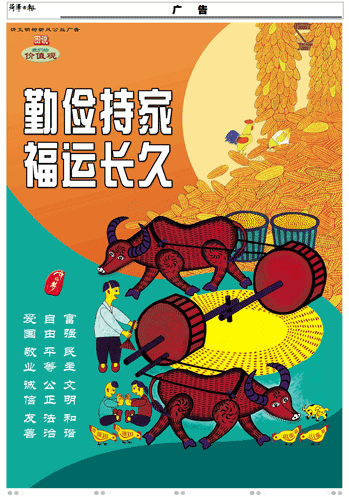□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孟 欣
在鲁西南地区,提起“吹响器”的巨野陈集“陈家班”,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自从8岁接触唢呐、梆子、小鼓等“响器”,现年已经54岁的鲁西南鼓吹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建彬,见证了近代鼓吹乐的兴衰演变。3月10日,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赶赴成武县南鲁集镇史庄行政村,见到了正在为一“主家”白事演奏鼓吹乐的陈建彬。
承载着乡情记忆的民间音乐
当日上午10时许,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驱车赶至史庄村,踏着雨后泥泞的乡村小路,记者终于在一辆展开了“舞台”的小型六轮农用车上见到了正在吹唢呐的陈建彬。
“白事不比喜事,台上中间可以稍停一会再接着演奏。”陡一见面,陈建彬略显歉意地让记者来到舞台上的一角。整个舞台,除了较为齐全的乐器和音响、电子屏设备,其余的设施则略显简陋。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尽管屡次登上省级、国家级舞台,以陈建彬为主的“陈家班”主要谋生地还是两处——结婚的人家、有白事的人家,且绝大多均是行走在偏远乡村。
记者了解到,鲁西南鼓吹乐是由民间吹奏乐器与打击乐器配合演奏的一种民间器乐种类,以唢呐为主,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济宁、枣庄、菏泽三市及周边地区。唢呐是鼓吹乐的特有乐器,主要依赖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而存在,是山东鼓吹乐中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在我国享有“唢呐之乡”的盛誉。
“今天6点多就从家里出发了,离家也就17公里,不过明天还要去济宁金乡的一个村演奏,估计早上5点就得出发。”陈建彬告诉记者。
“今天,唢呐班收入1200元。这是跟主家之前就商定好的,按人头算,每人200元。”据陈建彬介绍,红白事雇唢呐班,是包括巨野县在内的鲁西南的习俗,陈建彬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但从清朝起,他们陈氏家族便世代吹唢呐了。
“唢呐能广泛流传多年,源于它是比较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陈建彬说,唢呐演奏时可以不用话筒和音响,坐着、站着、走着都能吹,喜悦的曲子、忧伤的曲子都有,且通俗易懂、容易让人产生共鸣,适合于红白事。
12岁登台独奏挑大梁
现为陈家唢呐班班主的陈建彬,自八岁就开始系统学习唢呐、梆子等鼓吹乐器以及演奏乐曲的技艺。“十二三岁时就可以独立演奏了,然后像父辈一样在农村接一些婚丧娶嫁的活。在农村叫‘吹响器’,那时候的演奏上不了台面,只要村民听着舒服就行。”陈建彬说。
望着身后承载着全部家当和舞台的小型六轮农用机动车,陈建彬陷入了回忆,“那时候哪有这么多设备,就一辆自行车和几个木箱子,哪里有演出就骑行到哪里。济宁、河南等周边省市都去过,碰到雨雪天道路泥泞,就是扛着自行车和乐器也得一脚一个泥坑地赶过去。”陈建彬说,“刚开始学艺时,就怕冬天,因为那时候练功都要天不亮就得赶至村外空旷的农田里练乐器,还不能戴手套,手上的冻疮一层压一层,根本就没好过。现在虽然条件好了不再冻手,但每到冬季手还是痒得不行。”
“记得那是我20多岁去成武县汶上集镇演出,大冬天连着演出了2天,没有棚子更没有舞台。打梆子的时候,手上的冻疮被震得全裂开了,流出来的血甩得全身都是,可再疼也坚持着一场场演出。”陈建彬回忆道,“不仅仅是手,就连脚也是一到冬天就冻得‘胖’了一圈,鞋根本穿不进去。还记得汶上集镇演出那次,晚上住在那里起夜去厕所,可脚怎么也穿不上鞋,挤进去也不能立马走路,只能踩踩、跺跺让脚适应。”而这仅仅是陈建彬早年众多艰苦演出中的一个场景。
“那时候村民娱乐项目基本上没有,戏班子一去演出,能让他们高兴小半年。每当听见大家的掌声、叫好声,我这心里就暖乎乎的,再苦也值了!”陈建彬说。
从鲁西南农村走向更大的舞台
2013年,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陈家班的鲁西南鼓吹乐《唱大戏》,以精彩震撼的表演,荣获“群星奖”奖项,此后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目录,一步步从鲁西南的农村走向了更大的舞台。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鲁西南鼓吹乐除受电视、手机、电影等传播途径的冲击外,本是倡导丧事从简、喜事新办这一移风易俗行动也在“误伤”着鲁西南鼓吹乐在民间演出。被列入各级非遗名录、在城乡各处流传多年的唢呐调,无形中正遭遇新的传承尴尬。
“从古至今,唢呐的传承很大程度依靠婚丧嫁娶。”陈建彬认为,应充分认识唢呐这一民间艺术的价值。
坚守初心,传承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