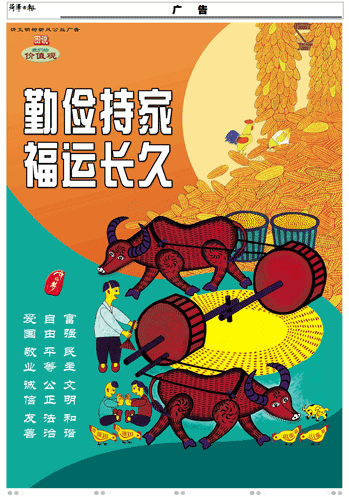我的母亲叫孙先英,生于1949年,真正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她饱尝艰辛,沐浴甘露,亲身经历了火红年代凯歌行进的豪迈,感受了文革荒诞至暗的十年浩劫,也见证了祖国改革开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风风雨雨走过了七十二年。
母亲出生后,是家中九个子女中靠清汤寡水和命大存活下来的四个娃之一。母亲没有童年,更没念过书,仅仅在村里扫文盲时端着煤油灯上过几天的“识字班”。母亲年轻时在生产队是个标准的“铁姑娘”,干起农活儿来如风卷残云,修田、推车、锄秧、收割,干啥都没落过后,每天挣得工分比男劳力还多两三个。媒人将母亲介绍给父亲时,父亲正在县上师范。言语木讷的父亲只给爷爷奶奶回了一封信,说现在都是新社会了,无须家人包办。言外之意,父亲是拒绝这门亲事的。可爷爷奶奶中意的是母亲的泼辣能干和敦厚率直的人品,所以就应允了媒人。
父亲毕业后,分配到了外乡一个偏远的村庄当教师。父亲和母亲的婚礼简单而又符合那个年代惯常的程序,父亲借了一辆自行车就把我母亲驮进了家门。
后来,母亲接连生了我们兄弟三个。我懂事的时候,常记得母亲用独轮车推着我去地里干活,那时我家承包了十亩责任田,母亲硬是用独轮车一车一车地把半亩薄地填上了一层七八厘米厚的土。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时都相继跟父亲出去念书了,自然家里沉重的负担就扛在母亲一个人那瘦弱的肩上。在我幼小的心里母亲身上总沾满了黄泥巴和一身的疲惫。母亲常说:“我不识个字,可不能屈了孩子呀……”母亲的铮铮铁骨和勤劳,支撑着我们全部的尊严和价值。我们兄弟三人发奋读书,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都考上了大学。一家供出了三个大学生,这在世代与泥土打交道的小村庄曾掀起了一阵波澜。
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我家的生活也逐渐殷实起来。记得那年,母亲饲养了二十多头大肥猪出栏后,她喜滋滋地抱回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也是我们全村的第一台电视机。自从我家买回这台电视后,到我家看电视的人那叫一个多,屋内挤不下,只好把电视移到院子里,嫌院内人多挤得慌,有人干脆攀到院墙顶上。而我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大街上的群儿之首,就连以前欺负过我的几个大孩子也主动向我套近乎献殷勤,只为我能同意他们到我家看电视。
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有我们兄弟三个小时候穿的鞋子差不多都是母亲自己做的。童年的我,最爱听的也是母亲纳鞋底的声音。每天晚上,在土炕的油灯下,我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母亲那“嗤—嗤—嗤”的纳鞋声。母亲一会儿把针尖从发髻上划一下,一会儿紧紧刚上好的鞋底,许多次我都情不自禁地抬起头看见油灯下母亲那专注的神情,是那样的和蔼与慈祥。
参加工作后,我们三人回家的次数日渐减少。如今,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母亲独守着乡下的老宅,我和两个哥哥数次劝她跟我们进城居住,但母亲执意不肯,她说根扎深了,哪也不愿意去了。每次回老家看望母亲,她总是早早坐在村口的磨盘上等我们,那佝偻的身影显得异常瘦弱单薄。母亲一边说有一两个月没回来了,又一边说工作要紧别老想着家里。母亲一次比一次老了许多,一头略显蓬乱的灰发,褐色的脸上刻着道道饱经风霜的皱纹,浑身贴满了膏药。每次看见母亲,我心中总有一种生活的沉重感,这种感觉至今让我在工作上不敢奢想浮漂。离开家的时候,母亲坚持送出很远,我总是一次次回头向她摆手,鼻子酸酸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那天走出电影院,我想着母亲,想着一个女人从羊角辫的少女变成一头白发的耄耋老人,突然明白了电影《你好,李焕英》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每一个儿女的成长,都有一个“李焕英”在身后守候呵护,千千万万个“李焕英”,用真与善,用她们的坚韧与柔软,谱写了一曲曲深沉而博大的奉献之歌,那就是无私的母爱。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并诚挚问一声:你好!